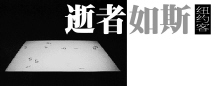
表述时间,古人一言以蔽之,那叫绝响。当然这不是指说话人最后一句话,是说这几个字令后人徒望洋而兴叹,换许多花样,却总显得重复,像是跟人学,望尘莫及,稍逊风骚。两千多年,也许比这还要长,古今中外艺术家一直挣扎着要表现的,无论什么题材什么技法什么媒介,就是时间。在空间中流过的没头没尾不是水也不是气的东西,在这莫名其状的东西里人事物处于某一时刻的存在状态。
眼下正在纽约路灵奥古斯丁画廊展出的,是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的近作,展览标题口气非常大,很虚,叫做生命之全部。谁不想理解生命的全部?哪位艺术家不希望见微知著地表现自己所理解的生命的全部,哪怕被评论家楞附会上去呢?可是谁都未能、不会、将来也未必能永垂不朽,能理解能表现的,不过是局部是片断是残片一般的细碎感觉。
拉开画廊大门往里走,眼前一团漆黑,得暗适应一会儿才敢奔里走。转过前台右拐,一瞬间,四块极其明亮鲜艳的颜色冲入眼眶。这四块颜色,波兰红、深蓝、橙红、天蓝,都像平躺在地上,只有面积,没有体积。尺寸一样,每块大概相当于国内最常见经济型单元楼小卧室地面那么大,十平米左右。比例一样,三比四,没有宽银幕没有遮幅的时候放大院电影那种银幕的模样。投影机悬挂在屋架下弦,镜头冲下,把影像投射到地板上,不对,是投射到离地面一个踏步高的木制平台上,走到矩形色块边缘,咚的一声,脚尖碰到地龙骨。这样一来,在完全没有自然光没有人工照明——放像机除外——的展厅室内,四块颜色仿佛悬浮在空气之中,游移在人的踝骨以上小腿肚子以下。
第一眼先抓住四大色块,然后就看见每一块颜色上又有各种各样颜色和大小的阿拉伯数字,像水中鱼和蝌蚪一样在同一平面上游动。可以很自然想到,这大概又是所谓数字化的把戏,画面如同电脑显示屏幕,数字嘛就是数字。再注视两秒钟,发现色块的边,好像变成金鱼缸的四个竖直玻璃面,人站在高处俯视,这些阿拉伯数字像热带鱼,一碰边儿迅即扭头,跟球儿似地弹回来调个角度接着游。这种碰边儿扭头的速度,人一般情况下不具备,想象一下让大夫用小锤儿敲膝盖测反应灵敏度或者被人掐了麻筋儿,或许比较接近这些数字在一瞬间变角度同时也变数的感觉。
打在矮平台上的是光色,纯度和亮度,传统颜料甚至工业涂料比如车漆,都没法与之相比。平涂一样的色块极其均匀,画面没有深度透视感。坐在电视机或者电脑显示屏前,光线从里往外射。油画和不用光箱的摄影也包括雕塑作品,光是从观者的身后上下左右投到作品表面,反射回来到人的视网膜。眼前这一组作品,虽然成像道理与电影放映一样,但是纯白色平滑台面不透光,好比到银幕背后看不到形象,悉数被反回来,在明亮同时,又让人感到它深不可测,即使把手伸进表面的膜也探不到底。数字尺寸大大小小,又制造了深度幻觉,仿佛透视讲的近大远小。浮现在眼前的,似乎是天文馆星体运行演示,数字像大小星球一般走太空步。
当得到这个联想,马上联系到宇宙是无限的。这种被矩形边沿框住的局面,没有足够的气势,它太有限了。能不能就让有的数字从边沿滑出去消失或者异地再现?让没出现过的数字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又悄悄溜进来?热带鱼一样碰边儿扭头,给作品增加了游戏趣味,平添一股俏皮劲儿。
在觉得俏皮的同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无奈,一种无法占有全部时空只能拥有局部片断和瞬间的无奈。这与展览的标题恰成鲜明对照,大反差。
还有一个连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也许穿凿附会的联想,但既然想了自有道理,也索性不藏拙。那就是,日本是个四面环水的岛国,很快到海边,只有回头才是岸,否则只能向大海深处漂去,其实在岸上、在边沿之内也是漂着的感觉。那里的人,对边界对时空或许有些长在陆地面积又广袤的地方的人所不具有的独特敏感,跟别处的人不一样的孤独和忧伤。
说过半天还没交待完毕,这组作品叫做《漂浮的时间》。
往里走,第二展室,《葡萄酒中的反声音》。左中右三面实墙各投一幅画面,是录像,二女一男各操英、法、西班牙三种语言,一会儿把脸埋入沉浸在脸盆的葡萄酒里,一会儿抬起头边倒气边数数儿,一到九,九到一,再而复始。抬起来的演员脸上往下淌着红色液体,有时候显得氧气不足,越讲越慢越含混不清,像是有点儿醉了。念一遍,扎一回猛子。
再往里走,又是一团漆黑,在第二展室体验到的明适应转眼又变成暗适应。在虚空中,两串儿亮点,一串红一串绿,形成两条螺旋线。它们是一堆电子表盘串成的,数字排列和出现顺序看了半天也没觉察出规律性。
宫岛1957年出生在东京,年轻时在东京国立美术音乐大学攻习油画。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发光二极管(L.E.D)当作媒介,电子表、微波炉、汽车表盘这些工业产品就是材料。可人们能记住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产品,而是红红绿绿的在无声闪烁的数字。他的这类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国际上的关注,1999年被选入威尼斯双年展,代表日本。
在作品中用发光二极管,容易让人想到用类似媒介创作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詹妮豪策尔。两相比较,豪策尔的作品像是芭芭拉克鲁格尔的电子版,尽管前者动后者静是常见情形,而且都不发声,但是她们作品的文字内容,都像革命性极强的充满批判或者冷嘲热讽的口号,单纯看文字内容,不用配音,脑海里都仿佛能听见震耳欲聋的声音,非常好战,别看是女艺术家,很有进犯性。而宫岛的作品就显得极其安静,没有文字,只有抽象的数字,还都是单数一位数。想想豪策尔的作品,宫岛的作品没有表现主义色彩,更像极少主义雕塑。这种沉静与喧闹急骤与舒缓的根儿上,也许是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起决定性作用。
宫岛自己解释过,他的作品中不用零,只是1到9,零是死寂终止,而生与死不过是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本身。正像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一样,作品同时表现人类的生存和生命本身。
这样的见解,对中国人或者说泛点儿对东方人而言,一点儿也不难理解,甚至缺乏新鲜感。话虽这么说,当你面对这些由抽象数字组成的作品,配上纯净明亮的颜色,就会获得某种神秘的感觉。这些数字,谁都认识,它们在浮动在闪烁又说明什么?各自代表什么?放在一起构成无数的瞬间状态又代表什么?也许,跟它们孤独地存在着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个结论太空太笼统,人们禁不住要去联想去探究去揣测去编造那神秘面纱之后的意义。正因为无法解密,无意义的面纱才显得动人,也更散发着神秘。这就是我们能看见能感受到的世界,即使这生活不过是人类有史以来有人以来无数次重复中的一次,而且心里明白它还会这么重复下去,力求解密的欲望却无法消除。我们觉得宫岛作品的意思或许正是在这里,它们其实没有意思,只是变换一种演示生存处境的表演形式,就连发光二极管当媒介,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种作品盯着看时间长了,就跟坐在电脑前目不转睛一样,很累人,绝不是休闲的最佳方式。在离开画廊之前,感到腿酸眼乏眼球发涩发胀,还能知道自己会疲劳,至少说明在此时此刻自己还算是活着,无论空间多大时间河流多长,还活着的感觉,就是此时此刻我能拥有的生命的全部。
